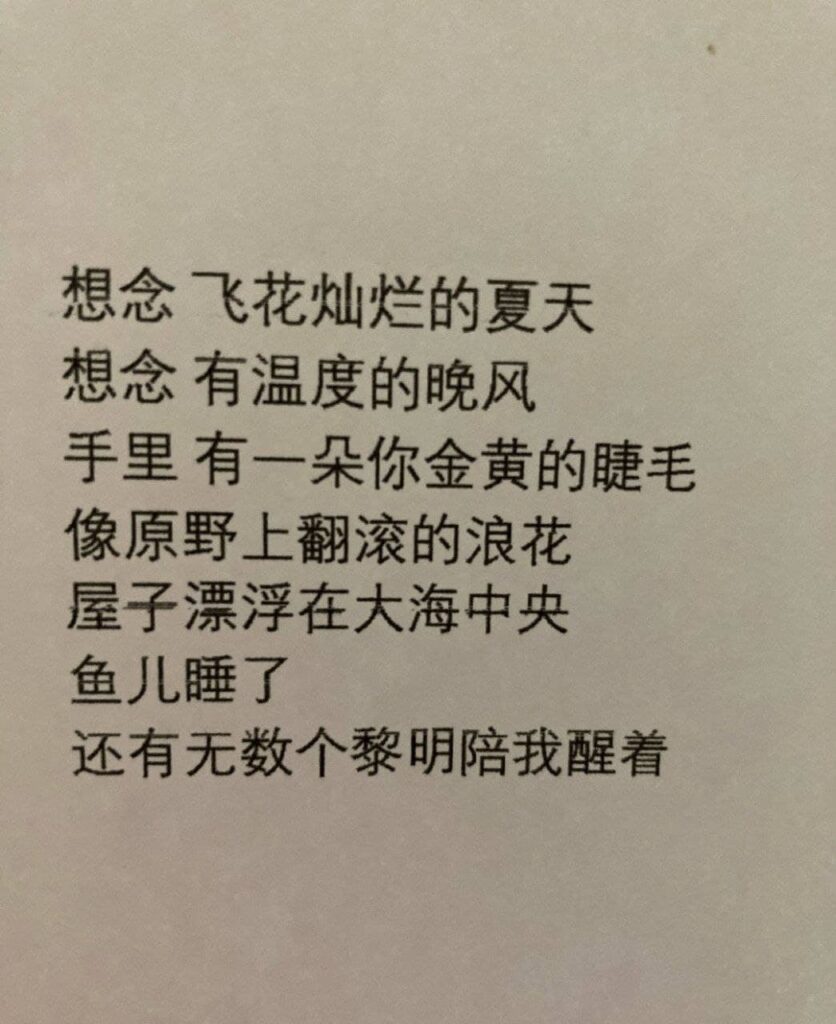二十四年
![]()
九月七日,飞机上晕沉沉地度过了十三个小时。走出LAX呼吸到一口新大陆空气的时候,我很难描述脖子以上发生的化学反应,就像是电影里主角要踏上勇敢的征程的时候,就像是游戏里的人物走出新手村闯向世界的时候。那种喷涌而出的多巴胺,澎拜高昂而实际不存在的背景音乐,都被我一口气吸进胸腔,再在脑子里像烟花一样炸开。夏夜的洛杉矶,潮湿又有温度的海风,第一次飞奔在60号高速上,City of Stars 的灯火在身后慢慢黯淡,美好的生活正在开始。
接下来的三个月,一切都像梦境一样的美妙。我爱自己狭小的房间,享受开车去学校的短短三分钟,喜欢实验室的氛围,就连在国内碰也不碰的subway也觉得十分可口,傍晚去往停车场的路上,会给悦悦打5分钟电话,讲讲身边发生的故事。感恩节,我road trip去了大峡谷,去了犹他,拍了夏夜银河的星空。22岁的我在不紧不慢地享受生活。
悦悦圣诞节前来到了洛杉矶,我们开车穿过LA downtown的大街小巷,从完美落日的Venice到人声鼎沸的Malibu,从雾满山岚的Topanga到雨后湿润的Riverside。当美好的事情频频发生在你身边时,你就开始处处留意一切细小又值得回忆的东西。就连洗车也感叹水珠散在空气里漫射出的彩虹有多美丽。

二月,疫情来临,加州宣布Lockdown,学校被迫远程授课。我以为疫情对我没多少影响,至少悦悦在加州陪我的这几个月,疫情没有太多地改变我的轨迹。我们依旧买菜做饭,去沙滩晒太阳,在院子里喝酒。当悦悦走后,我才意识到疫情打乱了生活,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,远程上课的同学们都隔着一层玻璃,街上的行人们也隔着一层玻璃,病毒把本来就脆弱的人类信任变得更加不值一提。一年过去了,我认识的人只限于实验室师兄们(谢谢中琪,唯一一个我不在Lab认识的朋友)。
看Friends的时候偶尔想起我国内的朋友们,在上海求学的峰峰,在广州上班的泡泡,留守在成都不愿出四川的人们。我就开始想念家乡的风和云,厚厚的云,没有一点点太阳的影子。四川就是加州的另一个极端,没有沙滩,没有阳光,雨下个不停。我开始意识到乡愁究竟是什么,是味蕾里一种淡淡的苦涩味道,是一种皮肤的灼烧感让你不适,是一些过去的人和物成为刻在记忆里的符号。
闲下来问峰峰,“要不要一起玩Dota”,有些人在上学,有些人在工作,有些人在另一个时区,慢慢我只有我自己了。
八月,悦悦回国了。她说她爱我,但我没有爱回去。“我爱你”最好的答复可能是“谢谢”。谢谢一个人的爱,就不用许下承诺,知道自己办不到就不要勉强。当一段关系慢慢进入到这个“我爱你”的阶段,我就开始逃跑,疯狂地逃跑。所以上两段恋爱的终结都源于她们想要一封情书,我当然会写情书,我是罗曼蒂克之王,但情书就是一个“我爱你”的证明,我当然不能爱你,我要逃跑。
我会短暂地爱一个人,也能长久地爱一个人,但最终都会爱上别的人。逃跑大概是出于自我保护,不用承担责任总比承担了又让人失望来得好。即便爱情不是个好东西,我还是相信爱情的,我只是不相信自己。
后来date了一些女生,我喜欢约会,大家都是忙碌的成年人,舍得挪出时间share给你都是真诚的人类感情。我慢慢喜欢上这种短期crush的感觉,大家都不是爱负责的人,暧昧就好。但是我一暧昧就上头,无时无刻不在想她,想要聊天想要拥抱。众所周知,身段是暧昧里不能放下的东西,舔狗是禁忌,这让我浑身难受,我想要见她,我想要闻她发梢的香味。唯一能解决这种浑身难受的方法就是快速crush上另一个人,我下头太慢,但是我上头很快,这是消灭荷尔蒙的有效方式。
一月,我在赶paper的due,每天四点睡八点起,生活起止于卧室的床和客厅的桌子。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开始慢慢模糊了,Work from Home最初是很美好的,这些人在疫情之前被称为数字游民,指不拘于办公地点四海为家的人。但是Work from Home一年之后,我感受到的是混乱和幸福指数的下降。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,娱乐和学习混为一谈,人可以一个月不出门,开始厌恶家里一切。在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赶完这个due后,我进了一趟医院,“胸膜炎”,不是什么大病。但是人类这个生物机器的脆弱性真让我吃惊。我开始重新晚上10:30睡觉,8点起床健身环。周末开去洛杉矶拍点花花草草,就像我刚来的那三个月一样,我的生活是一个人,但是也同样美好。